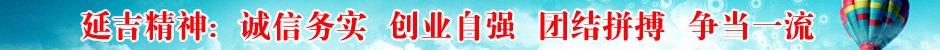如果要對“階層固化”作一個事實判斷(是否發生,程度如何)的話,那么,確定的標準是什么呢?除了論爭雙方各自簡單枚舉的個案和個人有限的觀察感受,反映普遍現象的論據又在哪里呢?
所以,“階層固化”,也許不是一個在事實層面可以簡單干脆地得出結論,從而一下子讓對方閉嘴的話題。凡是投入到這場討論中的人,應當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那么,一個議題難以確認基本事實,就失去了討論乃至關注的價值了嗎?
當然不是,而且也不會。
“階層固化”是一個社會整體的議題。人們關注這個議題,本身就是對社會整體的關注。那些憂心于這個議題的人們,往往已經從自己的觀察或生活中得到了與此相關的客觀真實信息。我想,這是我們對這個議題,乃至對這個議題下的不同觀點,應當先有的態度。人們說到的階層固化,即使是一種警世的危言也有價值。
在這個意義上,那種否定存在“階層固化”的觀點,盡管其初衷是擔心人們失去奮斗的信心,也決不應當漠視人們對奮斗機會、奮斗回報的憂心——就像“失去奮斗,房產再多我們也將無家可歸”這樣的表達在強調奮斗價值的同時,卻可能漠視了奮斗中的年輕人對住房的熱情一樣。
從認識的角度來看,我們應當看到,簡單枚舉的論據,其論證效果是有限的,它們可能已經使討論陷入僵局。我們應當放棄在簡單枚舉的論據之上輕率建立普遍判斷的自信。但卻不放棄通過開放的、可自我修正的討論,逐步收獲點滴共識,收獲積極的社會效果。
那么,除了可靠的普遍性數據,又有什么可以幫助我們的討論擺脫“個案僵局”呢?我覺得,應當看看個案背后是什么?在個別的、不確定的事物之中,有什么普遍的、穩定的東西?
馬云、王衛、劉強東,這幾個成功者的極少數個案,固然不足以作為判斷階層是否固化的充分根據。但是,他們成功的道路都提示了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市場。他們都是在市場上從底層一路奮斗成功的。在當代中國,市場是與體制相對的,更廣闊、更活躍,也更充滿機會的領域。通常看來,它也比體制更難以“固化”。在這個意義上,馬云、王衛、劉強東,甚至加上王寶強,他們代表的不是某個可以作出普遍性判斷的“比例”——足夠大或微不足道,而是某種“性質”。
市場的“性質”,天然具有廣度、深度和活躍度。它不只在高端成就馬云還有那幾位;也在中端、低端改變更多的人。正是因為有了比體制更為開闊的勞動用工市場,我在河北農村老家一個表妹的兒子,雖然只是考入了一家“三本”高校,在北京的邊上上學,畢業后還是得以進入北京的一家信息企業謀職;而同樣來自河北農村的表妹的女兒,也在轉了幾家企業打工的過程中通過了自學考試,現在在中關村一家互聯網企業做財務。他們在北京還沒有住房和戶口,離馬云、王衛、劉強東遠著呢,也不能作為階層沒有固化的論據。但是,他們卻通過自己的努力,經由市場,在一定程度上穿越了我與他們之間的“階層隔板”——即:我生下來就是城里人,而他們生下來就是農村人。
這種“階層隔板”是體制性的,它目前還包含福利政策差異,但它至少在“物理距離”上被這兩個年輕人穿越了。他們還年輕,只要這個社會保持著市場化,只要平等、開闊的市場空間逐漸取代被體制隔絕的空間,他們就有機會縮小與我之間的距離。當然,我和這兩位年輕人之間的差距也許根本就談不到是“階層”。我也不愿意承認這是“階層”。但是,這個社會大多數人之間的所謂“階層”,恐怕都不是指自己與馬云、王衛、劉強東、王寶強之間的差距吧?
如果說“階層固化”可能有一些分散存在的、個體感知性的判斷標準的話,那么,作為一名高校教師,我恰好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到其中的一個標準,那就是:如果我在一所國內較好的高校中,在我自己的教室里,還能夠不斷看到來自農村地區、貧寒家庭的學生,我自己就難以確定階層已經固化了。因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古今中外不都是人們穿越社會“階層”的通道嗎?
當然,正如人們所擔心的,他們即使上了大學也不能保證一定改變命運,穿越階層,因為階層固化可能就表現在沒有權勢家庭的孩子大學畢業后也找不到工作或好工作。但我們談到的這種“權勢”,難道不是體制性的嗎?
當然,即使是在市場上,人們也會有固化階層的傾向。最明顯的作為遺產的資本。人們也會通過市場化(因而差異化)的教育把自己的資產優勢注入到子女的教育中。這種固化傾向,就是人的本性了。
我們可能需要先搞清楚:社會要警惕和防止的階層固化到底是什么性質的——是體制性的,還是人性的?然后再考慮:我們可以做到的是什么?
而就我自己來說,我之所以“固化”在現在的“階層”上,而沒有能夠“向上流動”,我自己清醒地意識到的原因:是意志力和奮斗的沖動不足,而不是別的。(馬少華)
http://www.achalm-nug.net/uploadfile/2017/0427/thumb_150_105_20170427025650314.jpg
掃描二維碼關注
延吉新聞網官方微信公眾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