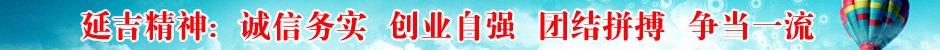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民事部分)紀要》,明確用人單位以“末位淘汰”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屬于違法。
“末位淘汰”指的是工作單位根據自身總體目的和具體崗位目標,設定一定的考核指標體系,以此為標準對員工進行考核,根據考核結果先后次序淘汰位于末端的員工。這種績效考核管理方法最早由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前CEO杰克·韋爾奇提出,它有利于增強員工的危機意識和競爭意識,從而為企業創造更多財富,為此曾備受追捧。問題是,不少企業家為了將“末位淘汰”機制的潛能充分激發出來,進一步增強員工的危機感,逐漸習慣在簽署勞動合同時擅自增加“根據‘末位淘汰’制決定解雇或繼續任用”等條款,這就違反了國家的相關法律規定。
“末位淘汰”從引入我國開始便飽受爭議,由于它不是一個法律概念,法律中并不能找到直接批駁它的法條,不過我們不難發現,其同《勞動法》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基本宗旨是相矛盾的。《勞動法》第39條、40條規定,勞動者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和制度或者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經培訓或調整工作崗位仍不能勝任工作的,企業方能援引條款解除合同。顯然,解除合同的關鍵在于確定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可實際上“末位淘汰”并不能真實地反映勞動者的業務能力,它只能衡量一名勞動者在一群人中的業務排名。即有可能發生這種情況:一群員工均未完成業務指標,但依然排出了先后順序,位于最末端的員工最終成了替罪羔羊。還可能發生這種情況:一群員工業績均相當可觀,且已完成目標,可只要是排序,他們之間總能排出個先后次序來,這樣,雖然位于末端的員工同樣優秀,卻不得不遭遇被解雇的命運。即使現實生活中有員工愿意接受這樣的條款,從實際影響看,“末位淘汰”也造成了一部分員工就業狀況不穩定,擾亂了社會正常的就業秩序。
最高法院的這份《紀要》并不是規定了一個新的法律條款,而是重申了一個早已存在的法律事實,即“末位淘汰”違反了《勞動法》相關規定。之所以一度有人否認這一事實,恐怕是因為《勞動法》同樣規定了企業有制定內部規章制度的權利,這些規章制度在不與國家法律相違背的情況下有一定效力。也就是說,如果某些企業僅僅將“末位淘汰”制作為考核員工能力的一項參考標準,而非以此決定其未來任用狀態,那么這種受到限制、修正的“末位淘汰”就是被允許的。其實,綜觀一些機械實行“末位淘汰”的企業,其效益并不理想,畢竟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環境下,員工與員工之間只存在劍拔弩張的關系,很難形成有效合力,這就削弱了其團隊協作能力,最終勢必影響到企業自身的效益。許多企業管理者恐怕也曉得“末位淘汰”不合理、不合法,只是為了強迫勞動者多賺取利潤、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等,遂昧著良心實行這一套吃力不討好的辦法。
《紀要》從一個側面提醒企業管理者,與其挖空心思鉆法律空子,不如實打實地引進更人性、多元的科學管理方法,努力營造和諧的企業文化,增強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在企業內部形成“先進幫后進”的氛圍,只有這樣才能把企業做強、做大,最后實現雙贏,而不是雙輸。(施經)
http://www.achalm-nug.net/uploadfile/2016/1206/thumb_150_105_20161206014425527.jpg
掃描二維碼關注
延吉新聞網官方微信公眾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