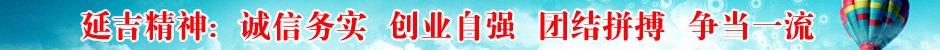背景:近日,有內部人士向媒體爆料江西省某鄉鎮的社會撫養費支出明細,2013年該鄉鎮征收社會撫養費107.10萬元,其中10%上繳縣計生委,剩下的96.39萬元全部由計生部門支出,支出項目包括勞務費、津貼獎金、招待費等,甚至用來為計生干部繳納社會保險費用。
京華時報發表兵臨的觀點:2013年9月國家審計署公布的全國9省45個縣社會撫養費審計報告顯示,2009年到2012年45個縣向征收單位和計生部門違規撥付社會撫養費總額達16.27億,占總征收額的60%,另外還有三億多元未按規定上繳國庫,部分縣向鄉鎮返還的比例甚至高達90%。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給地方預留了大量的自由裁量權,尤其是社會撫養費的支出上,缺乏健全的程序規范和監督機制,容易為集體性“權力尋租”提供契機,成為制度性腐敗的溫床。因此,要杜絕社會撫養費收支上的違規和腐敗,必須加強對政府收支行為的制度性約束,并通過嚴格的程序監督實現陽光操作。
新京報發表觀點:三十多年來,中國為了征收社會撫養費支付了高昂的社會成本。雖然,每年也收不了多少錢,而且這筆錢主要用于支付征收成本。與當年被廢除的農業稅情況類似——得罪了老百姓,政府自身也沒有多少好處,這樣的政策往往就很悲哀。當社會撫養費很少用于社會公共事業,而是主要供養基層單位、計生人員,大家就會質疑:還有什么必要去征收社會撫養費?就目前而言,社會撫養費需要納入財政監管,也要公開接受民眾監督,讓大家看清其用途,評價其存廢去留。在全面放開兩孩政策的影響下,有必要積極主動徹底清理以往遺留的此類利益捆綁政策。這種切割,不僅是對民眾個體權利的尊重,也是國家人口政策轉型的德政之舉。
小蔣隨想:全面放開二孩后,各地并未出現生育高潮,說明如今許多國人沒有很強的“多生”意愿。而從世界經驗來看,生育意愿降低與社會發展進步休戚相關。一些低生育率的發達國家為了鼓勵生育,甚至會補助或獎勵生育的夫婦,由政府與社會承擔相當比例的養育孩子的費用。說這些對我們是不是“超前”?或許有那么一點。但是,既然計生政策可以并已經調整,誰能說社會撫養費政策沒有改革或探討存廢的空間?尤其是,很大比例的社會撫養費最終只是“養育”了征收者,這種“用途逆轉”必然會引起征收正當性的質疑。人們心中還有疑問——如果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計生部門不再能夠獲得“返還”,其“人頭費”等開支會不會沒了著落?對基層計生部門而言,征收社會撫養費算不算是“上級不給錢,只給收費權”?如果這種猜測成立,隨著人口政策的調整,計生部門恐怕也需要精簡機構、減員增效。
http://www.achalm-nug.net/uploadfile/2016/0427/thumb_150_105_20160427023706846.jpg
掃描二維碼關注
延吉新聞網官方微信公眾平臺
 |